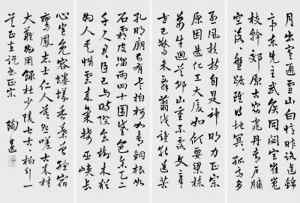汪精卫与南社“代表人物”说(2)
二、汪精卫诗词的成就及评价
汪精卫的诗词集名《双照楼诗词稿》,笔者所经眼者有四种:其一是曾仲鸣编辑本,民国十九年(1930)出版,分《小休集》上、下两卷;其二是民国三十年(1941)刊本,由日人黑根祥作编辑校勘,分《小休集》(上、下)和《扫叶集》。据此书跋文所言,其《小休集》上下卷当是本于曾仲鸣刊行本[②],而《扫叶集》则是汪精卫亲自交付的未刊稿。故黑根本经汪、曾、黑根三人之手,较为可信和精审。此本共计收录各体诗299首(其中译诗3首)、词27首。其三是陈群“泽存书库”壬午(1942)刊本,该本亦分《小休集》上下以及《扫叶集》,内容与黑根本相同,只是去掉了黑根的跋文,而将曾仲鸣的《小休集》跋置于最后(黑根本曾跋附于《小休集》下卷之末)。其四是民国三十四(1945)年五月“汪主席遗训编纂委员会”刊本,题作“汪精卫先生集双照楼诗词稿”(此本后来在香港翻印,书后标记“非卖品”、“蓝马柯式印务公司承印”),内容除包含黑根本全部之外,《扫叶集》增加了22首诗、10首词,此外还增加了“三十年以后作”32首诗、2首词。此外笔者还辑得汪氏散佚诗词十余首,以上总计约400余首。
汪精卫的诗作,最足以体现其革命志士胸怀的是狱中诸篇。除流传众口的《被逮口占》四首之外,如《狱中杂感》:“煤山云树总凄然,荆棘铜驼几变迁。行去已无干净土,忧来徒唤奈何天。瞻乌不尽林宗恨,赋鵩知伤贾傅年。一死心期殊未了,此头须向国门悬。”从明朝亡国起兴,表达了对民族、国家危难形势的忧患心情,最后又以革命者的气概准备赴死,并且预想革命的胜利,可谓沉郁顿挫。陈衍谓此诗最后一句“借用子胥语,痛切。”[6][p519]这一句后来还被陈毅在《梅岭三章》中借用[③]。又如《中夜不寐偶成》:“飘然御风游名山,吐噏岚翠陵孱颜。又随明月堕东海,吹嘘绿水生波澜。海山苍苍自千古,我于其间歌且舞。醒来倚枕尚茫然,不识此身在何处。三更秋虫声在壁,泣露欷风自啾唧。群鼾相和如吹竽,断魂欲啼凄复咽。旧游如梦亦迢迢,半灺寒灯影自摇。西风羸马燕台暗,细雨危樯瘴海遥。”此诗也大为陈衍赞赏:“自来狱中之作,不过如骆丞、坡公用南冠、牛衣等事,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,篇终接混茫,自在游行,直不知身在囹圄者,得未曾有。”[6][p519]
至于其砥砺志意之作,则几乎全是以牺牲一己为念。汪精卫很喜欢龚自珍的名句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曼昭谓“此两句实能道出志士仁人杀身成仁之心事。……其实精卫自所作,如‘雪花入土土膏肥,孟夏草木待尔而繁滋’,如‘飞絮便应穷碧落,坠红犹复绚苍苔’,亦此物此志也。”[2][p18]又如其《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》:“年年颠蹶南山路,不向崎岖叹劳苦。只今困顿尘埃间,倔强依然耐刀斧。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,莫辞一旦为寒灰。君看掷向红炉中,火光如血摇熊熊。待得蒸腾荐新稻,要使苍生同一饱。”也同样是自甘牺牲之语,此类诗句在汪精卫诗词中屡见不鲜,可谓三致其意。故胡适认为汪精卫有“烈士”情结[7][p601],可谓解人。而最能见其襟抱者,如其《杂诗》之一:“海滨非吾土,山椒非吾庐。偶乘读书暇,于此事犁锄。相坡莳花竹,欲使交扶疏。培塿凿为田,因以治瓜蔬。曾闻斥卤地,三岁不成畬。土膏未盈畚,石骨已专车。敢云心力勤,可以变荒芜。筋骨既已疲,魂梦或少舒。朝来视新栽,日照东山隅。多谢杜鹃花,使我衰颜朱。”革命肇造之艰辛,与夫革命者之心力志意,读来令人动容。这组《杂诗》一共八首,都是气格醇正,境界高远之作,古意盎然,直上汉魏。故其友人杜贺石评云:“读君之诗,使我感动。须知使我感动非易事也(杜为律师),我几欲自鞭辟矣。呜呼!”[2][p20]汪精卫的这些诗都可称“拙朴勇毅”,没有一般革命诗歌粗率叫嚣之病,故陈衍认为“精卫诗落笔必是自己语,不能移到他人。”[6][p519]
纪游诗在汪精卫的诗集中也占有不小的篇幅。这些作品有的清丽明快,有的刻画新颖,有的则于景物中感怀家国人事,也都不俗。如《碧云寺夜坐》:“馀霞灭天际,山寺渐沈黑。方庭蓄万绿,一一泼浓墨。岩壑入黝冥,深沈不可测。泉声出万寂,流远韵更彻。似闻穿林去,邂逅涧中石。微风一吹荡,松籁与之洽。”读之如闻声见色,令人悠然有出尘之想。又如《白松》:“秀林有奇松,玉树差可拟。孤高更皎洁,抗节比君子。岁寒餍霜雪,颜色亦相似。亭亭明月中,清影了无翳。临风得相见,缱绻不能已。何当如翠禽,乐此一枝寄。”表达了对“奇松”的高洁品节的赞美,以及自己欲化为“翠禽”,以一枝为栖而与之相伴的追慕之情。又如其《游春词》:“花枝红映醉颜酡,杂遝游人笑语和。我更为花深祷告,折花人少种花多。”“千红万紫各成行,日暖林塘蔼蔼香。此际园丁高枕卧,游人自为看花忙。”陈衍谓前者即《大学》“生众食寡”之义,后者大有功成者退,与扶杖而观太平气象。[6][p520]对于这些写景之诗,诚如曼昭所言:“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,惟天然风景,则取不伤廉,此苏轼所谓‘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……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’者。”[2][p17~18]然则这些诗篇不能视为一般的闲情之什,从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情操修养。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,作为革命志士的汪精卫,也有其感情深挚的一面,无论对同志、对家人皆是如此。如其民国后感怀革命之诗《十年三月二十九日,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下作》:“飞鸟茫茫岁月徂,沸空铙吹杂悲吁。九原面目真如见,百劫山河总不殊。树木十年萌蘖少,断篷万里往来疏。读碑堕泪人间事,新鬼为邻影未孤。”按黄花岗起义之时,汪精卫尚被系于北京狱中,此役失败,革命党人牺牲惨重,汪精卫于狱中闻讯,亦曾有作。此诗则为民国十年展墓之作,末句“新鬼”指汪精卫好友、同盟会骨干朱执信,民国九年牺牲,其墓与七十二烈士墓毗邻。据曼昭《南社诗话》记载,“时于右任督师三原,于报上见此诗,万里邮政一素笺,索精卫书之,悬于斋壁。”[2][p15]足见其感人之深。汪精卫幼年丧母,乃于1922年请广东名画家温幼菊为其作《秋庭晨课图》,以寄托其孺慕之怀。汪精卫为之题诗及序,有“庶几母子虽一生一死乎,于图中犹聚首也”之句,正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,情深语直,读之令人酸鼻,故陈衍谓为“伤心人别有怀抱”,“抵人千百”[6][p518]。又如其《冰如薄游北京,书此寄之》三首:“坐拥书城慰寂寥,吹窗忽听雨潇潇。遥知空阔烟波里,孤棹方随上下潮。”“彩笔飞来一朵云,最深情语最温文。灯前儿女依依甚,笑颊微涡恰似君。”“北道风尘久未经,愁心时逐短长亭。归来携得西山秀,螺髻蛾眉别样青。”诗题“冰如”即陈璧君,其牵挂、思念之柔情跃然纸上。“最深情语最温文”,正是汪精卫言情诗之写照。但是汪精卫并没有因为儿女之情而忘怀国家,如其《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》云:“依然良月照三更,回首当年百感并。志决但期能共死,情深聊复信来生。头颅似旧元非望,恩意如新不可名。好语相酬惟努力,人间忧患正纵横。”虽良辰佳日而时局之忧犹未暂忘,竟作此感慨语、牺牲语乃至不祥语,足见其情。
陈衍以遗老之身份,当时犹能不囿于党见,对革命者之诗称赏备至,可谓难得;而后人对汪精卫诗歌的评价,则别有意味。一言以蔽之,在汪氏沦为“汉奸”以前,是众口一词的赞誉,其后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贬损,其中的政治因素显而易见。且看柳亚子赠汪精卫的诗句:“清谈痛饮馀事耳,江山万里君仔肩”(《叶楚伧招饮,赋示汪精卫等》,1923)“来叩山中宰相家,招邀俊侣不辞赊。”(《十月二十八日,精卫招饮》,1923)“宋公园畔客皆至,黄石桥边人未来。越绝霸图劳使节,吴趋文宴失奇才”(《十一月四日,右任招饮宋园,精卫有事于浙不克至……》,1923)“珍重东山谢安石,风流宰相黑头公”(《是夜季新招饮,即席赋谢……》,1934),也曾推崇备至;其后则绝口不提,乃至以“曼昭”为汪精卫,加以贬摘[④]。